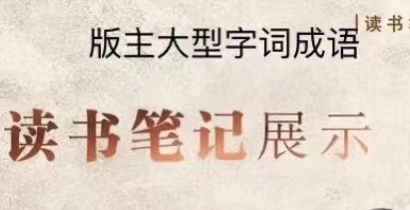从1988年6月份提出申请调动,经过两年时间到1990年的暑假两个人的调动工作大功告成。1989年宋力的高考成绩离本科线差了2分,如果愿意就读徐州师范学院这样的大学也可以被录取,当年师范院校并不吃香,宋力自己愿意再复习,正好我还在郑集中学,宋量量读初三。尽管张美兰已经到徐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上班,由于该校没有坐班制,她不但周末可以回到郑集,中间还可以在家里呆上一天,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照顾两个孩子的负担。孩子们经过一年的辛苦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工作调动成功,孩子们进入了理想的学校,确实令人高兴,说起来也让朋友们羡慕。可是就在1989秋到1990暑假这一年里我们也同时遇到人生以来最大的困难。祸福这一对双胞胎同时在这一年里降临到我这个四口之家。
张美兰到了经管学院工作不久,她母亲突然脑溢血摔倒,我们自然要花费精力照顾老人。首先是安排医院,到医院护理。出院后张美兰每周既要回郑集又要到琵琶山,来回奔波,非常辛苦。我要上课,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也是忙得不亦乐乎。1989年11月中旬,老人去世。疲劳加痛苦使得张美兰的体质明显下降。首先是胃病发作,疼痛难忍。最为倒霉的是在1990年的春天,她自己发现右乳房内有一小的肿块,就开始胡思乱想,担心长了肿瘤。到当时的公费医疗医院初诊,遇到了老熟人徐龙君大夫。他从徐州医学院毕业后先到马坡医院,后来到郑集医院,如今也到了市内,在这家医院上班,其调动的轨迹跟我们完全一样,见面后感到十分的亲切。他让我们到徐州二院进行穿刺检查。穿刺活检的速度很快,负责穿刺的大夫姓冯,他用一根很细的针头刺入乳房,吸出一点点活组织就到显微镜下观察,马上就把结果写在诊断书上。两个字母Ca使我们一眼就看出是cancer的首字母,那就是癌症。这突如其来的诊断结论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只好到徐大夫那里征求意见。徐说这位冯大夫还是很有两下子的。郑集医院的院长的癌症就是由他诊断出来的。那位院长不相信,到天津复查被否定了,但后来发展证明还是癌症,耽误了治疗。徐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肿瘤在身上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恨不能马上把它拿掉。
我首先到经管学院把这个诊断结果告诉张美兰所在的基础部的领导,要求请假治疗,然后就和徐龙君商量如何手术。当时我不敢想象可否到上海北京重新检查诊断,因为两个孩子面临中考和高考,我根本无法离开他们,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天大的困难自己顶着,这是我的个性。我回到郑集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姜理舜,他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在马坡时跟我学习英语的学生,如今已经是郑集中学的英语老师了。我让姜给两个孩子到食堂买饭,晚上关心一下,因为我要在医院照看他们的妈妈。徐龙君从第二医院请来了他的老师,中午要我们请一顿饭。我把经管学院基础部的两位领导请来作陪,因为我无法到场,必须在病床跟前。说来真窘,当时囊中十分羞涩。调入市内后最愁人的是没有房子居住,当时还没有房改,但对解决住房有些新的办法开始启动。经管学院的部分职工参与了学校负担城建部分的费用,私人出钱购买住房的队伍,我们也在其中。购买房子要我们提前支付一万三千元,而我们在郑集九年时间的储蓄总共为七千元(两个人每年的工资总收入1400元左右)。当时没有向银行贷款一说,我们向张美兰弟弟借了3000元,向郑集中学工会也借3000元,因此正是背债还款之时。请医生吃饭的钱哪里来呢?我想到了还有几百元的国库券,就损失利息提前支取交给了徐龙君替我办理。
手术后我就将摘除的乳房送徐州医学院病理室进行切片检查,第二天就拿到了结果,排除了癌症的诊断。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痛苦的心情也可想而知,这不是白白地挨了一刀吗?有的医生劝慰我们,拿掉彻底放心,这个肿块在里边以后发生病变怎么办?再说了也不能只听医学院的一家之言。我自然要到二院找姓冯的大夫,告诉他医学院病理检查的结果。冯坚持认为他的诊断是正确的。里边还有一个老大夫(后来发现还是张美兰高中同学,在美国当上医生的朱越的父亲),把穿刺的和病理检验的两个玻璃片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认为就是恶性的。他们的坚持使我对下面的治疗难以决策,如果是恶性的,就要开始进行化学治疗,如果是良性的就可以不进行任何治疗了。谁能给我做主呢?冯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诊断,那就找我的老师去。”他只告诉我他老师姓刘,是上海肿瘤医院的。我还得到上海去找那位刘权威去,这是不现实的,我实在抽不开身呀。
遇到困难就只好难为朋友了。我们同时想到让我们南大的老同学曹乃云想办法找到肿瘤医院的刘教授。曹乃云是我们学德语的同班同学,老家是通州三余的,跟我是地道的老乡,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毕业后始终十分知心,相遇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德语老师,让他去找肿瘤医院的刘教授肯定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曹乃云在收到我的信后发现了信纸上泪痕斑斑,使他感到事情十分紧迫。他脑子急转,想到了一个在上海的堂舅医务界有熟人,连忙跟他联系,对方回话说认识刘教授,可以把切片拿到他家里去让其观察。曹乃云喜出望外,要他舅与教授预约拜访。后来他们一起到了刘家,说明了来意。刘教授在显微镜下看了切片后说,“我有一个要求,希望病人不要找我学生的麻烦。”曹乃云和他舅舅马上答应了刘的要求。然后他说:“我的学生看错了,是小叶增生,并非恶性肿瘤。”得到这样的诊断,曹乃云的心里也就宽心了。他来信说,挨了一刀就算了,就当在马路上让汽车碰了一下吧,不要想了。
那段日子我忙得焦头烂额。两个孩子在郑集生活无法自理,特别是宋量量仅仅14岁,没有大人照顾患了重感冒,我晚上赶回学校找大夫给他输水,第二天早晨赶回徐州照顾病床中的张美兰。到了徐州想孩子,到了郑集想妻子,来回的车票成了一付扑克牌。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后出院,搬进了张美兰同学冯云培借给我们的小屋里静养手术伤口。
张美兰动手术的事情终于让南通老家的人知道了。大哥知道我们太需要人了,就把他二女儿宋国红带来帮助我们,可谓雪中送炭,让国红在郑集照顾两个弟弟,我可以定神在徐州照顾美兰,等其基本康复后一块回到郑集。手术恢复顺利,我们终于全部回到了郑集,南通兄弟姐妹全部前来看望,灾难终于过去了,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准备孩子们升学考试了。恐惧的日子大概延续了一个月的样子,我十分庆幸此事对孩子们的情绪没有造成太多的损伤。1990年暑假后一家四口人都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生活。张美兰乘校车到西关经管学院上班;我骑自行车到彭大上完课就可以回到小屋进行备课或写作;宋力到东南大学浦口校区报到就读;宋量量学会骑自行车到一中上学,中午也可以回家吃饭,高中三年期间始终在我们的呵护之下,免去了过早独立生活的苦痛。他太小了,高中三年的年龄跟爸妈初中三年的年龄相仿。
灾难过去了,但我对张美兰的这次手术心痛在胸,始终耿耿于怀,追恨难弃。白居易有诗云:“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这是我在焦头烂额之时所作的一个错误的决策。说焦头烂额强调了客观原因,对自己松绑原谅,错误决策的根子在于我的个性。我老是认为自己的果断爽当是一大优点,其实这个所谓优势招致了我犯下这个大错。我意识到在很多时候决策能够哪怕是慢半个节奏很可能就能够避免一些错误。如果我能够在动手术前再让一家医生穿刺一下,或把穿刺的标本让北京上海的医生判断一下或许可能避免这么大的一个冤枉手术。好在手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们做到了互不埋怨,对我们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所产生的伤痕,无论是看得见和看不见是永远抹不去的。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手术差不多已经过去了20年,我不敢用文字记录和描述我去徐州医学院进行病理检查的这段路程,也从来没有跟别人口头讲过这件事情,让其过去吧,不要折磨我了,让读到这段文字的人自己想象吧。我只能反复地在心中唠叨,放下无法改变的过去吧,做到事去而心随空。古人云:悔既往之失,亦要防将来之非。记为教训,好好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错误吧。
2010年1月28日于徐州风华园
2012年2月21日于芝加哥校对
2023年8月5日上传于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