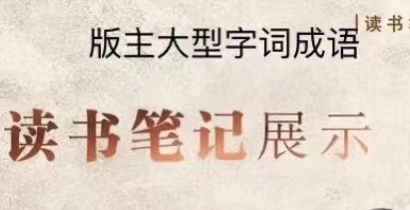从1967年秋到1968年夏是我们最为自由但又无聊的日子。串连活动停止了,我们也基本失去了对学生组织活动的兴趣。每天上午组织学习报纸社论,讨论形势,大家不敢不到,但都是马马虎虎,应付了之,坐一会就结束了,然后就各自活动。有人总结很多大学生也在参加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语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的资本主义路线):男生焊电路自装收音机,女生打毛衣也是线路。我这个人手笨,不能搞无线电,也不喜欢熬夜打牌累计积分,老是盼望复课闹革命,但这很不现实。我从系里弄到一台手提式英文打字机,用它也可以打德语,我的劲头来了。原先上课期间我看到老师用打字机备课,把复写纸按在上边一下子就能出来四份教案供四个老师使用,这使我很是羡慕。我要利用这个时间把打字的速度练上去,将来一定能够发挥作用。每天集体学习社论结束后,我就来到系部的一间小的地下室,开始了打字练习。一次张美兰同学询问我忙什么,我就带她到我练习的地方去看打字机,这个玩意儿对她也有了吸引力,就这样我们经常在一起练习打字,增加了接触,并开始了无所不谈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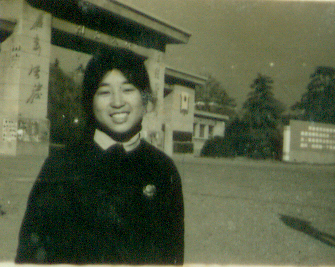
文革期间
她家住在徐州郊区,从小很是不幸。1948年底的国共两党间的淮海战役使她父亲失踪,她和弟弟由母亲抚养长大。好在她从小学习成绩优秀,靠着助学金,一路顺风直至大学。由于长期单亲家庭,经济的拮据超出我的想象,高中时全靠助学金生活。家里一点自留地里要种点山芋,妈妈买山芋秧子的钱都没有,她就周末回家带馍到学校吃,把助学金省下来给妈妈买山芋秧子。我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心里有一种预感,觉得如果能与她为伴,那我一定是找到了一个十分贤惠的一心一意的妻子,并同时给父母找到了一个孝敬公婆的好媳妇。没有任何浪漫式的一见钟情,完全是理智行事。当时班里谈情说爱的不少,但大多是在家乡进行或秘密地和外班、外系和外校同学接触,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三四岁的年龄,有的甚至到了二十五六了。丁班的丹阳人氏丁生根每天夜里出外侦察,回到宿舍后汇报侦察情况,报告某某女生或某某男生跟某某异性开始接触之类的消息,大家把他称作情报局长。按照这位丁局长的提供的消息,说明很多人确实已经行动。班里有两个男生回家已经结婚,也有人公开了自己的异性朋友。所有这些情况告诉人们,是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了。我也决定开始行动,向张美兰发出了一封书信,并静候回音。

张美兰接到南大入学通知书
1968年的麦收季节南京军区用卡车把我们拉到了安徽霍邱县城西湖农场帮助收麦。一个月亮皎洁的晚上,我把张约了出来坐到田埂上。她把小时候自己左胳膊脱臼没有能够治愈的事情跟我说了。我是个粗心大意的男子,从来没有关心她的胳膊,经她一说意识到她两个肩膀有点不对称。她把两个胳膊伸出来让我看到了不同的长度,左胳膊明显短了一点。我表示一定会好好照顾她,一定不让她做不能做的事情。她对我的为人、勤快和学习上的拼劲表示了赞赏。事情就那么简单,没有任何礼物互相赠送留念,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恋爱关系,而且是义无反顾,直到结婚组建家庭。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我的快刀斩乱麻爽快果断的作风与她的慢条斯理优柔寡断的个性偶尔发生些碰撞,在确定我们的恋爱关系时她却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决,也没有设置任何的障碍来考验我是否真心。幸亏她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的个性绝对不会像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男子为追求一个女子而去跨越千山万水,甚至被女子羞辱也能够勇往直前的人。这也确实说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非同一般。
从今后我们就形影不离了,南大附近的大街小巷几乎让我们踏遍;清凉山、莫愁湖、白鹭洲、祁霞山、燕子矶、玄武湖、明孝陵、中山陵、灵谷风景区等无处没有留下我们的身影。我们是典型的贫恋穷爱,估计中午不能回来吃饭就带上馒头,夹上榨菜。我们婚前的日子是漫长的,从1968年的初夏直至1971年春节结婚,接近三年时间,那确实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遗憾的是俩人没有能留下一张游玩的相片,因为那个年代照相机的只是极少数富有者的奢侈品。
2008年10月25日完稿
2023年8月4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