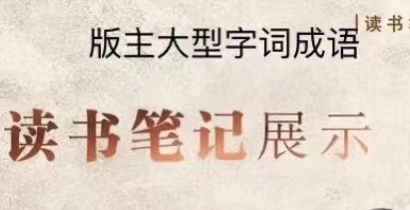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让我经历了。1966年6月1日6:30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天下午,南大溧阳分校的文科三系(中文,历史和政治)的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校长匡亚明在一本书里抹煞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当时匡校长就在分校,晚上他亲临现场看大字报,指着这张说是大毒草,指着那张说观点反动……。我正好也在现场,心想写大字报的同学要倒霉了,就像1957年反右那样要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匡的话音刚落,有的系就把人集合起来开始批判大字报的作者。6月3日上午的批判到了高潮,各系各班全面开花进行批判和整顿思想。可到了3日的下午,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来到溧阳批评了匡亚明打击学生的做法,宣布解放被批判的学生,形势即刻逆转。6月4日6:30分中央广播电台就播送了南京大学揪出了校长匡亚明的消息,就这样所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南京大学开始了。我们这些在溧阳分校的学生全部回到南京本部,整个南园贴满了攻击匡亚明和校党委的大字报,学校一片混乱。
接着省委派来了工作队,由省委副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可是不久又有人贴出踢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的大字报。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主张维护工作队的威信,其中包括贴了匡亚明的大字报,被工作队解放了的一些人。这些人被对方称作新的保皇派(在溧阳保护匡亚明的成了老保皇派)。我当时属于比较保守的,觉得把工作队撵走恐怕过火了吧。可是形势的发展又一次出乎我的所料。彭冲刚从北京出席中央会议回来,我校部分学生获得了消息就到了火车站,等他下车时逮个正着,并把他带到学校。学生纠察队围成一个圆圈,让彭冲站在中间首先在校园内游了一圈,最后让他表态。彭冲说毛主席批评了北京大学工作队,现在要搞的是大民主,我们应该充分相信群众,撤销工作队,你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吧,赢得了下边一片掌声。
大概是六月二十日左右,校园里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西安交大的学生遭遇镇压,呼吁大家到西安去支持西交大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真有点像解放前闹学潮的味道。怎么去呀,真难以想象。部分学生到了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要求省委支持南大学生的革命行动。到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说同学们已经在下关车站集合了要求上火车。我们班也有两个同学到了省委,估计也已经到了火车站。担心他们肚子饿了,我和马灿荣两人用饭盒带了点饭菜到下关车站给他们送饭。一到那边,看到我班的王新宽同学手里拿着个喇叭正指挥学生上车。我们给他饭菜,他不屑一顾,反要我们也到西安去。我和马很是犹豫,因为什么都没有带呀,怎能走出那么远呢。王鼓励我们不要怕,大家都是这样,走了再说,不会饿死的。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记得第一学期到南京江北的晓庄林场劳动时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我就和另外一个同样没有见过火车的同学一块利用休息时间来到了铁轨边想看一下火车的尊容。结果来了一辆货车,觉得丑得要死,但不敢再等客车了,担心劳动迟到,悻悻地离开了铁路。如今客车就在前面,不需要车票,只要自己同意马上就可以上去。这种诱惑着实让人抵挡不住,我和马也就随着人群上了前往西安的列车。
整车的乘客都是南大的学生,大家十分激动,非常热闹。一会儿传来消息,说已经有人到学校交涉借钱借粮票,乘坐后一次火车赶到西安。由于西安交大我有三个高中同班同学,所以心里有底。夏天,背心短裤头可以借用一下。到了西安不久就要我们去签字领钱和粮票,开始了自由串联活动。我和马灿荣到了西安的好几个高校,特别参观了当时校园很小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参加了一次揪斗西北局书记刘澜涛的群众集会,使我觉得西安学生的造反精神超过了我们,感到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全动员了起来。大概过了四五天的时间,我和马灿荣准备回南京。到了西安车站拿到了一张传单,上面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一九六六年坐火车不要钱,支持学生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觉得毛主席太伟大了,历史上的皇帝都是镇压造反,我们的这位领袖支持造反,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太幸福了。西安车站已经执行最高指示,凡有学生证者就可以获得你想去的地方的车票,如果学生证不在身边,校徽也可充当身份凭证。我们两个已经排队快拿到火车票的时候得知可以随便去哪个方向,而并非一定要回南京,使我们犹豫起来。我们从队伍中退出,在车站广场上徒步思索。两个人都非常想去北京,这是每个学生从小的梦想,但是我们两个是班级文革小组的成员,那天是送饭给在下关车站的两个同班同学,没有想到自己跟着他们到了西安,班里其他同学怎么看待我们呢?失去了去北京的机会何时才能重来呢?我们思前顾后,拿不定主意,就到了一家小酒馆,弄了一小瓶酒对吹起来以撒闷气。后来还是马灿荣拿定主意,回去吧,来日方长,北京将来是有机会去的。回到学校一看,很多同学自由结合分组行动各奔东西了。我们真后悔应该放开一点,到北京去看看该有多好。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模样
既然大家都已走了,我也和另外几个同学上了沪宁线,先到苏州,住在江苏师范学院(后来的苏州大学),除了看大字报,还游览了狮子林,拙政园这两个典型的江南园林,完全是一种身临红楼梦大观园的感觉。接着又到了上海,接待我们的是一家饭店,我首次住进了这么豪华的旅馆,有浴缸和卫生间,睡前还可以泡澡,全是免费的。我把几个著名的大学全部参观了一遍: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和外国语学院等等。

串联让我们五人一起游览了苏州狮子林
回到学校,发现第一批集体去北京串连的队伍已经出发(九月十日的样子),第二批准备到北京过国庆节,我连忙报名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大约九月二十四日的样子,我随着几百个同学出发乘火车到北京。在火车上文艺积极分子就拉着手风琴教大家学会了“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首新作的歌曲,内容反映了文化革命的主题。到了北京站我们很快上了迎接我们的汽车,并经过了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真是心潮滂拜,斗志昂扬。我们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着手排练准备参加国庆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主席。十月一日那天我们半夜就起床了,汽车把我们拉到指定的地点,天才刚亮。我们等啊等啊,差不多到了十一点队伍才开始行动。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到达天安门时队伍还是整齐的,可进入金水桥对面的长安街时,大家都停留在那里向城楼上看,寻找毛主席,队伍一片混乱。我没有看到他老人家,周恩来穿着一身银灰色中山装,特别显眼,他挥手要大家不要停留;毛的接班人林彪很瘦,我也一眼就看到了。等我们过了天安门,广播里播出了毛主席接见柬埔寨西哈努克的消息,这就解释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他的缘故。
国庆节后我跑遍北京的各大院校,北大、清华、北外、人大、北师大、北二外、语言学院、北工大、北农大等等,还参观了颐和园、北海公园、金山等从小十分向往的名胜古迹。很遗憾故宫是铁将军把门,没有能够进去,据说是害怕红卫兵到里边破四旧搞破坏。在北京足足半个月的时间,彻底满足了来首都一游的强烈愿望。
又回到学校,天气逐渐变凉,但很多同学仍在外地。中央提倡步行串连,向老红军学习。我和已经回校的几个同学碰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对步行到江西井冈山意见比较一致,于是就开始着手准备,想象一下应该带的东西,做好物质保障工作。我们买了一只钢筋锅,准备在无人区自己做饭吃。在一切准备妥当就要出发时,马灿荣突然有病需要手术治疗。怎么办?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我们六个先出发在省内长征,分别以六家为目标从苏北转到江南然后回校,这样差不多马就可以出院,我们再一起出发到井冈山去。
我们六个人打着南京大学经风雨长征队的旗子出发了:侯凤英(女)、祝逸清(女)、王传岳(男)、严秀中(男)、王星良(男)。从南京出发经过六合、仪征、扬州、宝应、高邮,首先到了建湖严秀中家;接着回头向南经过东台、海安、到了如皋的王传岳家;再走近路从平潮直接插到姜灶就到了我家;从我家到南通港过江到当时的沙洲县的县城杨舍镇(就是如今的张家港市),见到了王星良的哥哥;下一个点就是江阴华士王星良家。就在我们到王星良家的同时,马灿荣带着印度尼西亚的归侨姑娘林桂英一起跟我们集合了,队伍壮大到了八人。下两站就是无锡祝逸清家和镇江的侯凤家。从镇江到南京大家不想再步行了,就搭上了火车。这个时候已经是1967年的春季,连中学生都开始串连了,火车里挤得难以想象。我们互相帮忙全是从窗户爬进车厢的,行李架上,小桌子上都有人坐着,厕所里也满满的,进去后就不能动弹了。好在我们路近,远方的乘客非把尿逼到裤子里不可。
这次回到学校已经是1967年的3月,上海的造反派进行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南京的造反派们也跟着行动夺取了省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结果造反派内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个夺权好得很,另一派认为好个屁,前者简称“好派”,后者称为“屁派”,文字上用字母P换“屁”。大家都慌着站队,到底站在“好派”一边呢,还是“P”派一边呢?。我们长征队的8人也开始有了分歧,有的参加“好派”的一些活动,有的参加“P”派的活动,也有的索性当起了逍遥派,根本不可能再在一块统一思想步行长征去井冈山了。不过还好,尽管由于派别不同减少了来往,大家还算相安无事,没有发生当面辩论和情感上的伤害。
好P两派打打闹闹了好几个月,中央决定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也进了南大,很多同学也回到了学校。可是部分造反派又开始对军管会表示不满,1967年8月份整个南京举行了一次浩浩荡荡地反许世友大游行。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形势的发展让人捉摸不定,就连来到南大实行军管的省军区一级的干部梁杜吴三人也发生了裂痕,全校继续混乱。直至1968年10月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同军管代表一起进行了杀气腾腾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行动。开始是挖美蒋苏修特务,凡是解放前与国民党有牵涉的,出国留过学的都成了被排查的对象,其中有的成了专案组的审查对象;接着抓现行反革命,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学生遭了殃;在我们离校前又抓516反革命集团分子(所谓516组织,我后面第十三节要专门交代),把一批批造反派的头头一个一个地消灭掉。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学习班”,一旦进去就要你的命了。那时的南大不时地会听到学习班里各种自杀的消息:割脉、吃安眠药,跳楼等等,十分恐怖。
我开始感到迷徨,觉得这样搞下去能行吗?何时是个头。书不能读了,天天学习政治,读报纸后要求发言讨论,很多人没有了兴趣,但还不敢表示,只好混天了日。
2008年10月25日于墨尔本完稿
2012年1月31日于芝加哥校对
2023年8月4日上传于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