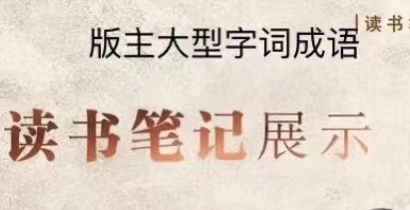高小阶段
小学四年级读完叫初小毕业,接着是要进行升学考试的。金余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也都是两个班,但乡下有几个村小都是初小,那些初小毕业生也要到金余来参加升学考试,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记得我们那一届是两个考一个,即50%的升学率。我是考上了,取得了上高小的资格,但外边传言说我考得不好,是袁平老师包庇的。袁老师已经是教导主任了,我也无法检验传言的真伪。袁老师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此事。我认为是某些人出于妒忌,因为班上没有被录取的人是很多的。
进入五年级后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放学回家开始主动帮助父母亲作些家务,寒暑假里看磨放牛也不觉得非常难受了。由于早上放牛,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以后我一向是先看书再吃早饭。父亲也不再对我那么凶狠了,对他的恐惧感也消失了。他的精力转向管理教育下边三个比我小的孩子。1952年大妹宋德群出生(奶名:金儿),1956年小妹宋向红问世(奶名:水儿),全家八口,我已经体会到父母的艰辛,总是尽可能地替替大人的手脚帮帮他们的忙了。
就读五年级和六年级时由于不排名次我不知道自己在班上的位置,但在六年级时大家投票选干部我的得票最多,因而当上了班长。其实这个班长也不能做什么,个头不高,担心自己不压众,有些心理障碍,很多活动自己也捞不到参加。我特别羡慕那些运动员,乐队的鼓手或号手。特别是县里举行小学生运动会,铜鼓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其节奏我是耳熟能详,自我觉得无需培训就能上阵敲几下,哪怕负责打那个不十分起眼的三角铃也行。可惜我永远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五年级时我们的班长好像比我大四岁的样子,留级过数次。暑假里他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居然能到南通南郊的狼山,照了很多相片,美极了。到六年级时他当上了全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才得以让我当了班长,但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参加夏令营如此好的待遇,心里充满了许多委屈。南通狼山是大人们每年必到的地方。在我们家开香店时我看到很多人从我们家买了香直接步行到狼山顶上给大圣菩萨烧香,来回60华里的样子,当天返回。父母亲以及叔婶舅妗等也去,回家后就在一起畅谈观光感想,把我馋的要命。他们还把大一点的孩子带去,先是哥哥跟去,接着是姐姐。我盼望长大,但到了可以上山烧香的年龄又因为要上初中住校还是不能去,我多么盼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到狼山去看看。

如今的金余小学
高小时我根本不敢想读初中的事情,因为初中很难考,整个金余街上能够上初中的屈指可数。再说上初中要到金沙,西亭或二甲去读,离金余最近的也有14华里,远的有30华里,住宿和伙食的开支也不小。正因为如此,很多家长索性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升学考试直接回家干体力活了。哥哥读到四年级,姐姐读了两年就停下来了,我已经读了高小了,超过他们了,还想读初中,我真的没有想过,尽管我非常羡慕那些周末坐着汽船回家的初中生。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同意我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而且到哪里去考试由我自己决定。我到过县城金沙,我想去一个没有到过的地方去,因此我自己决定报考金余东边的二甲中学。班上绝大多数报考金沙中学或县中,而到二甲考试的只有三个同学,由一个老师送考。其中一个叫刁允发,他大哥在二甲食油加工厂里。我第一次见到把大豆加工成豆油的规模颇大的加工厂。我们就吃住在里边,得到了刁允发兄长的全面照顾。
发榜那天,我赶到二甲中学,看到刁允发录取了,而我落榜了,但最后有备取的几个名字,我是备取五。 这表示录取生里如果有五个不愿意就读我才能顶替上来。这种希望太小了,农民的儿子当农民吧,认这个命吧。
我看到旁边还有一张二甲民办中学的招生广告,我读懂了其中的意思。凡是愿意就读民办中学的现在就可以报名,不需要再参加考试,根据二甲中学的招生成绩录取。我觉得自己是备取五,读民办中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到家后向父母亲如实报告,尽管考不上,但我没有任何压力,父母亲绝对不会责怪我。不能就读,回家干活,他们才高兴呢。同时我也把民办中学招生的广告跟他们说了。但我并不对就读民办中学抱有任何希望,准备停学干活了。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和另外两个家长商量一下决定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让我去二甲民办中学读初中。父亲认为我个头太小,不能干活。另外觉得备取五,说明成绩还可以,到民办中学肯定是名列前茅。就这样,1958年小学毕业,到了秋季我开始到二甲民办初中就读了。
整个小学阶段最让我怀念当然是袁平老师。我是一个农家子弟,他对我的偏爱完全是出于教师对我这个学生的一份情感,不图任何回报。作为老师特别喜欢某些学生,并且建立了终生友谊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其实一个具有职业道德的教师在各方面会特别严格要求他们喜欢的学生,绝对不能做一些让别的学生觉得厌烦的事情。偏爱在教育上是一个让人忌讳的用词,但我还是用了。我说的这种教师在情感上对某些学生的注重和个别老师对有权有钱家长子女的偏爱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事情。在我的教师生涯中也偏爱过很多学生,学习成绩并非唯一标准。另外师生感情是双向的,你喜欢的学生,他(她)不一定领情;你不喜欢的学生有可能对你一片深情,永远把你留在心中。我对袁平老师这份怀念一直保留在我的心中,每次回家总要去拜访他。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没有送过他任何贵重礼品,也从来没有同桌共餐过。跟我同桌共餐的人数实在记不清了,美酒佳肴卡拉OK乐曲,谄媚赞美之词不绝于耳,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任何生命力,早就烟消云散。袁老师的一生很不平安,一个小学的教导主任在文革中居然也受到了冲击。文革结束后小官衔恢复原位,但不久就患病卧床。病重期间我来到他的床边,得知是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导致瘫痪,在上海由名家动手术也不能痊愈,刚过60就散手人寰。写下这些文字深表对他的思念。
2008年10月14日于墨尔本
2012年1月27日校对于芝加哥
2023年8月3日上传网站于徐州